中国法院对所谓“人工智能主体性”态度暧昧,其他国家的处理却相当严格。2018 年美国有一 件牵涉 “黑猩猩自拍照”的版权案件,法院认定 “非自然人不具有著作权法赋予的法定地位”。[7]此案涉及的动物和机器都不是自然人,因为它们虽然可能 “具有感知能力”,但是不具备 “能够反思自 身行为的意志能力”。只有自然人 ( 包括由自然人依法形成的法人)能有权拥有被注入人格的物,即“财产”,主体人格是财产权产生的前提。
立法保护版权的目的,是 “鼓励发明创造”,著作权法要求被保护的作品,具有独创的外在表 达,是创造意志的产物。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 “自由意志”? 一般认为 “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工智能无 法自己发起生成符号过程”。[8]但是有的国家开始承认 “电子人”的法律人格,因为 “某些电脑程序 开始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这种做法导致今后社会秩序出现二元: 自然人权利与人工智能权利共 存,二者可能一致合作完成某工作,也可能互相推诿,如上述 “百度侵权案”; 如果它们的法律责任 (例如侵权、诽谤、违法言论) 发生冲突,此时人类法律若偏向人类一边,会造成类似种族与性别歧 视的 “机器歧视”。
智能实际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性客观的,按照因果逻辑做功能化解释、学习、推理;另一部分是感性主观的,给出的不是功能化的认知解释,而是直觉与感情的反应。人工智能的意义方式是基于算法的客观活动,能处理理性部分,却无法处理感性部分,而偏偏艺术注重的是后一部分,即感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在只管效率科技(包括智力竞技,如围棋)方面高歌猛进,在艺术方面举步维艰。哪怕生成物能通过图灵测试,即产品让接受者无法分辨究竟是人工智能创作还是人的 创作,对人工智能艺术的帮助始终不大。
本文第二部分所引关于人工智能艺术的诸种例子,都已经成功地“骗过”读者、观众、编辑、甚至艺术专家。但可以看到,虽然人工智能艺术品可以表现出感情,却是通过算法模仿的结果;人们始终要求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人格的显现,即个人心灵形成的素质与敏感性,或个人经历带来的民族性、时代性。就此而言,人工智能只是工具或被雇佣的执行者,它的生成物至今只是设计算法的生成 物: 作品的权力和责任都必须由雇佣者、设计者、选择展示者承担。
人工智能在未来究竟会不会具有艺术创作的主体性? 未来虽不可测,但是我个人对此深表怀疑。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优点在于实用与效率,而艺术的目的是反其道而行之: 降低效率,减缓认 知速度。艺术与游戏相似,是对科学/实用表意进行效率的反冲,是以无目的为目的。在本质上,人工智能艺术为设计者的目的服务,以设计者的目的为目的。哪怕在艺术创作中,人工智能进行的依然 是非艺术的活动。康德认为人与物的区别,是人本身具有绝对价值,人的本性凸显为 “目的本身”。因此,不管是艺术的 “无目的的目的性”,还是当今泛艺术化的 “合目的的无目的性”,都只有创作人才能具有,只有接收人才能欣赏。[9] 人工智能只是模仿与延伸人类已有的艺术,有“创造行为”而无“创造目的”,因为只有人才能制造与欣赏认知困难这样一种 “反目的”。
正如阿尔法狗能赢棋,但做不到能赢时故意放水输棋,不管是为了不让对手过于颓丧,还是奉承要面子的上司,抑或为了吸引对方更进一步爱上这项游戏,这些对于人工智能而言都过于复杂。“放 弃赢”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元语言,需要一种反逻辑的思维方式,一种超越理性平面的情感投入。[10]而且,棋坛已经发现,阿尔法狗在收官阶段比较随意,有的人解释收官太复杂,超出其计算能力; 也有论者指出: 阿尔法狗的预定目的是赢棋,只要赢半目就是赢,它就不计较繁琐的收官能赢多少目。人工智能必须另作操控,才能“反目的”,变成算法可控的 “扭曲”目的,才有可能获得 “制造认知 困难”这个艺术创新的基本目的。
4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易评鉴难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和判断力大可怀疑: 2019 年程序 “一叶·故事荟”评价《收获》杂志40年来刊登的作品,总结出六种类型,这表现了它的特长; 但程序“谷臻小简”从2015年全国各文学刊物的 771 篇短篇小说中选出 60 篇佳作,就与批评名家的选择少有重合之处。要求人工智能作为艺术评判者,实际上比让它进行创作更难。
为什么鉴赏与判断那么重要呢?人工智能艺术创作速度奇快、产量奇高,可以日夜工作毫不疲劳,只消耗一点电量。就数量而言,几台电脑就可以供应全人类需要的艺术品,这当然不可能,艺术本身需要多样性。因此艺术市场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选择,这项工作不得不由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来做。小冰的一本诗集,是策划者从它的几万首诗中选出来的。小冰的诗究竟是谁写的呢:是小冰,还是背后的选家?这种争端以前也发生过:大半个世纪以来,多位猩猩、海豚、大象“画家”,都有过杰作面世,都有过拍卖成功、被收藏的记录。这些聪明的动物只要有食物鼓励,就可以不知疲倦地工作,那些 “成功”的作品,是从无数被人丢弃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缺乏艺术家主体性支持的 “艺术品”中,能给予作品以艺术意图性的,实际上是选家与展示者。这些人工智能生成品成为艺术的最重要关键,是展示为艺术: 可选的数量极大,总能够找到几首读起来似乎有诗味的作品。机器的诗集、画集、音乐、小说,都是这样选择出来的,没有 “精心创作”,只有精心挑选。
人工智能艺术史或艺术批评,也会落到这种窘境,即材料丰富,分类仔细,但缺乏判断。2012 年纽约著名的 MOMA 艺术博物馆用人工智能产品举行了 《发明抽象艺术》( 1910-1925) 展览,扫描艺术家与城市联系的地图,找出艺术家与同代人的关系,然后用令人信服的数据找出艺术家与时代的连接性,及其对艺术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这是一种有人工智能大数据支持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用数据可视化、主题建模、模式识别等方法,在理性的目的下做得非常有效而且精彩。但是艺术史家不能奢求能用这种工具研究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穿透现象寻找潜在规律的操作。[11]因为历史运动需要对材料的穿透性阐释,需要对艺术作品的同情性敏感,也需要对时代潮流的理解力。人工智能艺术软件的设计者,必须让电脑在扫描学习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风格流派进行标注(例如书法 “颜体” “柳体”等) ,这样“学习”量虽然大,但能够分类鉴别,不至于产出大杂烩,或过于平庸,或把不同风格糊成一片,成为笑话说的“输入垃圾,产出垃圾”( in, out) 。
更重要的是,艺术欣赏从来就不是一种严格的认知,而是一种 “错觉” () 。这个命题从 1959 年贡布里希的名著《艺术与错觉》开始,渐渐为艺术理论界所认同。贡布里希指出:视觉错觉、心理错觉,以及两者联合形成的综合错觉,三者结合才出现艺术欣赏所必需的“错觉的条件”。[12]近年维纳·伍尔夫更推进了这个命题,他指出艺术错觉是由沉浸 () 式体验与理性距离 (dis-tance) 两个相反的元素构成的,是文本再现与观者理解在适当语境中的结合。其中关键是观者的 “准经验性”。艺术品不需要与生活经验对应,但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呼应,才能激活观者的想象力,创造出逼真感。这种欣赏既不是概念错误,也不是感知错误,而是 “再现的艺术指导脚本在精神屏 幕上投射的原始资料”所引发的艺术感觉。[13] 艺术的接受和欣赏需要接收者的 “准经验”,例如看到 银幕上的怪兽,激发我们对野兽的经验,然后我们才会悚然而惧。
那么,人工智能作为艺术接收者,有可能具有经验或 “准经验”吗? 有可能悬搁理性距离,让 自己沉浸于艺术文本制造的错觉之中吗? 显然不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经验是人为读取已经 “形式 化”了的别人的经验文本,不是它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果这些经验材料有标记 “真”或 “假”,它们就是真实的真,或真实的假,不会引发艺术欣赏所需要的错觉。艺术的 “假戏假看中的 ‘真戏真 看’”[14] 对于人工智能是要求太高了,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人工智能实现从感情的吸引,到认知的沉浸,到进入更高一层的 “逼真感”的复杂心理过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工智能如何能对自己 的生产物的 “艺术性”做出判断呢? 如果最后的甄别、筛选、展示,依然要靠人类来做,人工智能 还有艺术主体性吗?
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艺术程序,从GAN软(,生成性对抗网络)进化成CAN软件( ,创造性对抗网络) 。GAN 包括两个对抗性程序: 生成器、鉴别器。生成器只管生成新图像,而鉴别器判断哪些可以是艺术,其标准是训练时“学过 的”的巨大数量艺术品图像。而 CAN 分设两个鉴别器,一个决定 “是不是艺术”的底线,另一个决定 “生成物属于何种风格类型”,标准依然是读取过的图像。第二鉴别器删除不属于既成风格的作品,以避免产品 “过于创新”,得不到人类社会艺术界的承认。机器只是设法让生产品符合人类社会 “当今”获得盛赞的艺术标准,它找不到可以尝试 “突破欣赏者接受惯例”的离奇风格。与上节讨论人工智能是否能故意输棋一样,它能做到,但是必须事先设计寻找自我失败,而这样就违反了人工智 能本身的目的性。
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总会对重复旧有风格感到厌倦,而人工智能就像临摹赝品为生的匠人,不会有厌倦感,也不会有创新冲动。旧有数据的归纳,无法得出创新的标准,创新本身才是艺术生命力之所在,但是艺术创新是靠各种不成功的冲动喂养出来的。
5人工智能艺术的未来
一篇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艺术理论探索,应当给未来留下余地,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太快速,无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以上所说的人工智能艺术的种种问题,也并不是因为笔者保守,拘泥于今日暂时的局面,发牢骚作挑剔。笔者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艺术正在撼动艺术学理论的一些基础立足支点。本文最后一节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而且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回应。
人工智能艺术据称造成了 “后文科”的出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发展潜力,形成了所谓 “新 工科-文科”的结合学科。自从 2002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建立 “新媒体艺术与设计系”, 宣告了人工智能艺术的蓬勃发展。理工科学者关心文科,古已有之。20 世纪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有 发聋振聩的重要人文理论著作,例如 1944 年薛定谔的 《生命是什么》、1950 年维纳的 《人有人的用 处: 控制论与社会》等等,而文科学者靠近科学或工程学,效果有限,最容易发生失误。1998 年 《社会文本》杂志上刊登索克尔的 “诈文”,“超越界线: 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出了大洋相。很可能更多的作者没有自我揭穿,反而得意于他们玩弄概念的把戏。
因此,文科学者只应当讨论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关联,对人类前途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操 作原理与设计,对于这一行当之外的任何人(包括文科学者,也包括其他理工科人士),都是一个黑箱。最近人类学家徐新建提出建立 “新文科”,其核心是 “推动哲学与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 合”,介入性科技革命,实现彼此间互补共建。[15] 他说的 “新文科”明显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使 用数字时代出现的新技术,已经卓有成效,上一节讲到的 “数字艺术史”就是个明证。基于大数据 技术的社会科学,催生了不少雄心勃勃的计划,让社科理论界视野豁然开朗,而 “后人文”似乎至 今没有启动。一些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关系的讨论,例如本文,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后艺术学”的探讨。但是“数字艺术学”还只是一个课题。虽然这课题已经热闹起来,最近三年这方面文章发表之多,令人惊叹,但是至今没有开创出 “后艺术学”这门学科。“后人文”并不是想阻拦人工智能 的发展,而只是评估今日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文化的影响,揭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对人类文化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
“后人文”应当研究的第一个重要课题,是 “后媒介时代”(也可以译作 “后媒体时代”) 是否已经来临。关于 “后媒体时代”最早的理论著作,可能是柏林大学教授齐林斯基的著作 《媒体考古学》。[16] 此书提出媒体发展四阶段论: “媒体之前的艺术”( 岩画、口头讲述、歌舞) ; “附带媒体的艺 术” (短距媒介: 书写、各种纸绢、壁画) ; “凭借媒体的艺术” (长距艺术: 印刷、广播、电影) ; “媒体以后的艺术”(数字化媒体) 。为什么称作 “媒体之后”? 因为媒体变成了艺术创作的主体,人工智能自己创造艺术。本文的讨论证明此说言过其实: 数字技术至今主要还只是媒介的升级版,艺术 创造的主体依然是艺术家。只是媒介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某些装置艺术 ( 用电子设备与其生成物做艺术载体) 可以说已经把媒介与艺术载体合二为一。
“后人文”可能探索的另一个课题,是 “艺术的终结”。这不是一个新命题。黑格尔、斯宾格勒、贝尔廷、卡斯比特、丹托,都曾郑重其事地提出 “艺术终结论”。艺术作品的 “艺术性”已经被历史所抛弃,听起来像是一次次的 “狼来了”,因为艺术的生命力似乎越来越顽强。近年许多论者提出: 日常生活的 “泛艺术化” (pan-) 也导向 “艺术终结”,因为艺术与生活将归于同一。

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加强了这种 “艺术终结论”,甚至有论者提议,既然人工智能艺术生产效率如此之高,不如让人工智能管创作,人类只管欣赏。[17]本文上一节已经提出艺术创作不可能与欣赏脱节。本文的详细讨论已经证明,不管人工智能在什么程度上从人类艺术家接管艺术创作的责任,艺术作为人性的最彻底表现,一如先前并没有终结。马克·吐温说:“我从不希望谁死去,但很喜欢读某些讣告。”各种“艺术终结论”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因为艺术中的某种东西恐怕真有死亡的可能, 但是只要人类没有终结,艺术与人类同在。
由此出现的第三个相关问题,听起来更加惊世骇俗: 即将或已经占有这个世界的是 “后人类”。后人类如果有艺术,当然是人的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凯瑟琳·海勒提出: “当你凝视着闪烁的符号能指在电视屏幕上滚动,不管你对自己看不到却被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什么样的认同,你都已经变成了后人类。”[18]这话说得有点玄,她的意思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靠网络,我们的意识靠无数的信 息存在于全世界,因此我们都已经是网络人,网络即是我们的主体存在之处。因此网络世界中的人类,如果需要艺术,也是人工智能的艺术。
“后人类”讨论的往往是一种 “进步”的报复。在教权神权时代,人只是神权的奴隶。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福柯说 “人是近代的发明”。[20] 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人的地位至高无上,使人性高扬。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赞叹说: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 ”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人文学科是哲学的中坚学科,整个“进步”进程都围绕着人性的解放,是为了增强人的理性尊严。后现代主义开始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解构“关于人的神话”,但是生态主义等,依然是在调节人类的“过度文明”,是人的自我纠错。直到“人工智能 威胁到人的一切优点”,才出现了“后人类”时代的可能。[20]意思是人工智能不会有人的各种缺点。
但是人类的优点是否能完全被替换呢? 人工智能至今没有反思能力,也没有艺术能力,今后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替代人类。因此,艺术似乎应当是 “后人类”最无法撼动的领域。人工智能是逻辑构成,而艺术追求感性;人工智能追求共识,而艺术鼓励歧义; 人工智能服从设计,而艺术尊崇创造; 人工智能艺术或许有感情表达 ( 例如初音未来唱的情歌,或是小冰写的情诗) 但那是人云亦云学来的冰冷感情,是对人类作品中感情表露方式归纳的结果。艺术与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来说,是背道而的。从这个观点来看,艺术是人性的最后根据地,是人工智能催生的 “后人类”传染病的抗体, 是针对 “反人类病”的解药。
有些艺术家,包括中国艺术家,比艺术理论家更热衷于“后人类”概念。例如在2019 年第三届广州艺术节的座谈会中,策展人张尕表示: “后人类是一种生态平衡、万物共生的概念,人不再居于主导地位,而是一种生命形态。”作为例证,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王郁洋举出他的一件作品: 把 《圣经》还原成0与1的堆集。这似乎在呼应上文中海勒对 “后人类”的定义: 人已经变成信息的图像 像素。但是参加座谈的德国艺术理论家海因茨-诺伯特·约克斯却反驳道:“你放弃了一个艺术家作为控制的体……你用一种反乌托邦的方式展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彻底改变。”[21]这个例子,当不能作为中国或西方艺术家或论者的代表性思想倾向,我只是想说,“后人类”风暴刮晕的,远远不只是西方艺术理论家的头脑。
或曰: 人工智能正在飞速发展,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少未来学家的看法是: 等到 “奇点”出现,假定是30年后,超级人工智能出现,它就会具有主体性,就会对艺术创作负起全部责任,自己进行发起、设计、选择、展示等环节。因此,我们讨论的是尚未出现、但可能出现的局面。
对30年后的事,什么断言都是猜测。笔者非常同意哲学家塞尔的论断: “程序不是心灵,它们 自身不足以构成心灵。”[22] 塞尔的话是30多年前说的,在这30多年中,我们看到很多奇迹般的事件,但是人工智能有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质,以及人性的本质呢?包括本文列举的种种令人惊叹的人工智能艺术成就,没有一个事件足以让我们看到艺术的人性之光,在一个纳米级芯片中点燃。
参考文献:
[1]Louis ,Resume of a of ,( ed. and trans.) J ,: Univ. of Press,1975,p. 3.
[2] Dines , : A – to . : of Press,2002, pp. 174 – 288.
[3]倪阳: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评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书屋》2018 年第 8 期,第 15 页。
[4][以]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 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第 25 页。
[5][美]杜卡斯: 《艺术哲学新论》,王珂平译,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 12-14 页。
[6] Danto,After the End of Art: Art and the Pale of ,,NJ: Press,1997,p90.
[7]曹新明、咸晨旭: 《人工智能作为知识产权主体的伦理探讨》,《西北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第 95 页。
[8]李琛: 《论人工智能的法学分析方法: 以著作权为例》,《知识产权》2019 年第 7 期,第 14-22 页。
[9]赵毅衡: 《为 “合目的的无目的性”一辩: 从艺术哲学看当今艺术产业》《文化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22 页。
[10] Dyson, ’s ,The of the ,New York: Books,2007,p. 206.
[11] ,“ Art ”, for Art ,Issue 3,2018,p.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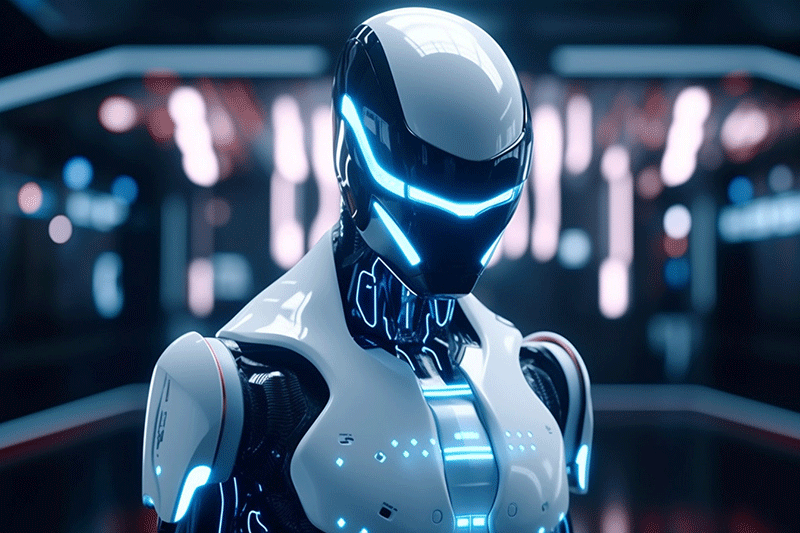
[12][英]E H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 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杨成凯校,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 社,1987 年,第 240 页。
[13] Wol,f “ ”,in ( ed) Wolf et al, and : in and Other Media,New York: Rodopi,2013,p. 24.
[14]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版,第 268 页。
[15]徐新建: 《数智革命中的文科 “死”与 “生”》,《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 期,第 23 页。
[16] ,Deep Time of Media: an of and by Means,tr ,Cam- MA: MIT Press,2006.
[17]马草: 《人工智能与艺术终结》,《艺术评论》2019 年 10 月号,第 140 页。
[18][美]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vii 页。
[19][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学科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 三联书店,2001 年,第 506 页。
[20][意]罗布·布拉伊多: 《后人类》,宋根成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8 页。
[21][德]海因茨-诺伯特·约克斯: 《艺术: 用技术的形式回应数字时代》,《社会科学报》2019 年 4 月 18 日第 6 版,第 2 页。
[22]John R ,Minds, and , MA, Press,1986,p. 10.
本文刊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5期
编辑︱郭家杰
视觉︱欧阳言多
往期精彩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
请点个“在看”吧